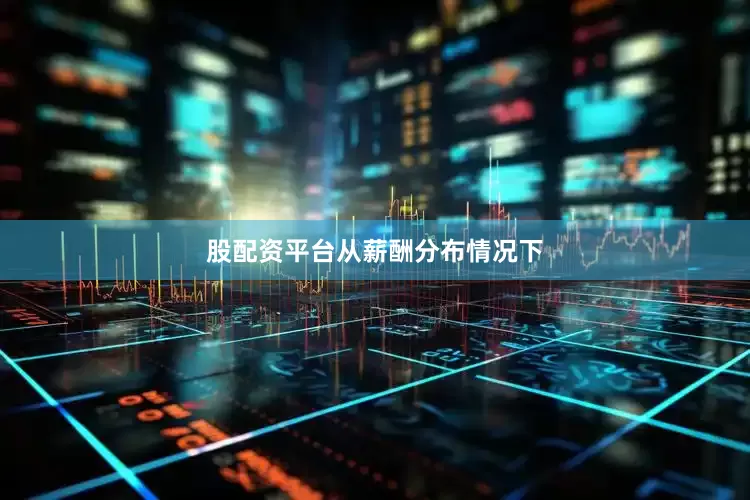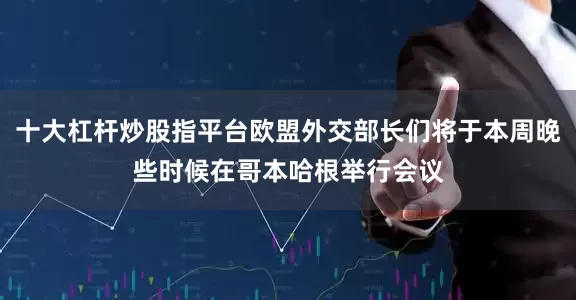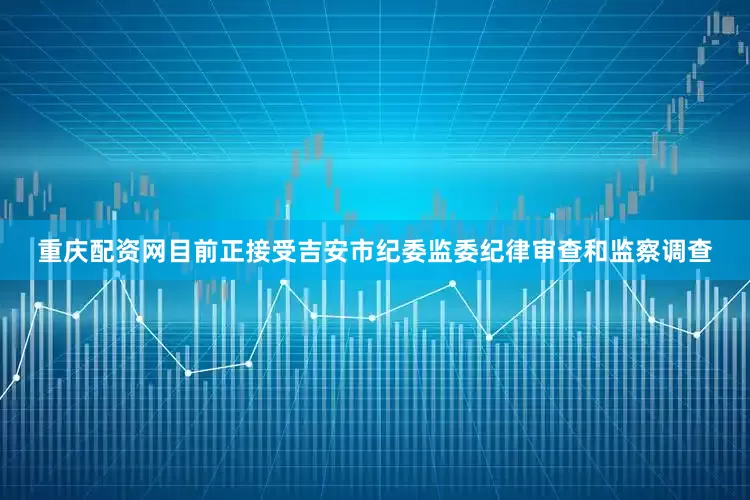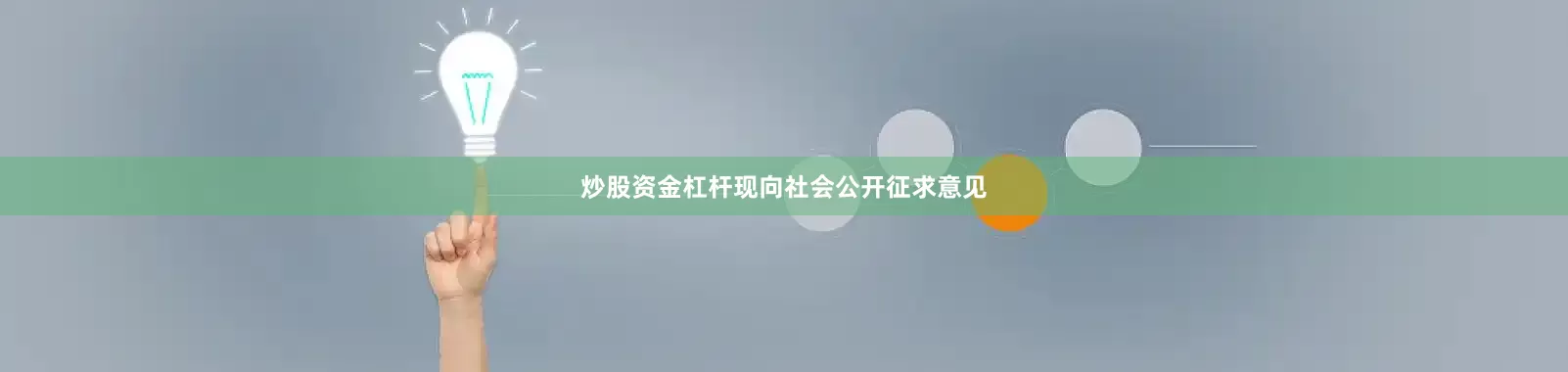“1979年11月,洛杉矶长老会医院,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台湾见他一面?”张闾瑛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压低声音,语气里带着几分责备和犹豫。病床上的摇了摇头,没有回答,只是把目光移向窗外的夕阳。

这句短短的问答,没有第三个人在场,却成为张家后辈传诵已久的话题。外人不知道的是,早在十多年前,于凤至就下定了“不再回头”的决心——那不仅是对婚姻的了断,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一道防线。
顺着时间推回1937年。那一年,于凤至被查出乳腺癌,西安事变余波未平,刚被押往南京,赵一荻留守身侧。为了保命也为了保全家庭,于凤至带着四个孩子匆忙登上前往旧金山的邮轮。人们常把这次远行视作治病之旅,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“撤退”。伤口不止在躯体,也在婚姻里。
在美国,她做过两次大手术,随后便定居纽约上州。战火在远东蔓延,她却第一次感到“耳根子清净”。那个时代的富家夫人多半没离开过东北平原,更不要说独立处理房贷、税单和子女教育,于凤至却一天学会西式账本,一天跑遍社区银行,她甚至跟邻居争吵谁家草坪该先修剪。张家旧里的人情世故,在纽约无处安放。

孩子们是她最大的软肋。长子闾珣在慕尼黑受精神刺激,判若两人;闾玗爱上烟斗,肺气肿迅速恶化;小儿子闾琪还没成年就病逝。接连三场白事击垮了一座母亲的心理防线。张家后辈觉得她“在躲”,其实更像是在逃避无法弥补的亏欠感。闾实后来评价:“她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,也没脸面回去面对伯父。”缺席的不是亲情,而是难以言说的负罪。
1960年代初,台湾当局提出让她赴台探视,附带条件是公开支持蒋介石对大陆的立场。于凤至始终没松口。她不接触政治,但绝不做政治花瓶。蒋家知道张家的长媳一旦站台,舆论会大不相同,可于凤至心里清楚,一旦签字,她的自由就此终结。那几年她干脆躲去加州,住进女儿闾瑛开的画廊后院,身边只剩护士和几本英文福音书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曾给张学良寄去几本《新约》,劝他皈依。“信基督就得与非信徒脱离”,这在教义里有明确说法。张学良点头受洗,下一步就是解除婚约。1964年离婚批文下达时,于凤至正在特拉华州做例行复查。律师电话通知她,她只是轻描淡写回了一句:“收到。”不是无情,而是意料之中。离婚给了她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,也堵死了回台通道。
有人认为她眷恋美国的富足,其实她最在意的是生活掌控感。试想一下:在奉天帅府,她是长媳,却必须时刻察言观色;在纽约,她可以穿着棉T恤推着购物车,没人盯着礼仪规矩。对50年代的中国女性而言,这种自由近乎奢侈。闾实多年后感慨:“大伯母赵四小姐画画,是在囚禁中寻找出口;三婶(于凤至)不肯回台,是在自由里封闭自己。”两种选择,没有对错,只是性格差异。

1975年,张学良获准迁居夏威夷,他主动写信邀她共度晚年,信里措辞平和:“过往种种,俱成旧梦。”信寄到纽约,她让女儿退回。谁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读完,但可以确定,她再也没提过“长春”和“少帅府”四个字。
1981年开始,张氏后人陆续到美国探望,她总会重复一句话:“别替我解释什么,也别替我评判什么,历史自有答案。”这句回避式回答让晚辈无从追问,却道尽她的处世逻辑——不澄清、不对抗、不回头。

三年后,她的病情恶化,住进洛杉矶医院。张闾瑛多次商量:“妈,能不能回去看看爸?就见一面。”她含笑拒绝。或许她害怕的是那座岛上重兵把守的高墙,更害怕回去后连最后一点自由都丢掉。
1990年4月20日,于凤至在加州病逝。讣告没有提及她的丈夫,只写了“前中国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之前妻”。两年后,张学良托人带来一束白百合放在墓前,没有署名。那天风很大,花瓣几乎立刻被吹散,仿佛他们之间最后的牵系也随风而去。
外界常把这段故事概括为“名门夫妇聚散无常”,但透过细枝末节可以看到,于凤至的“躲”是一种自我保护——身体需要治疗,心理需要缝合,政治风险更要回避。到了生命终点,她依旧相信,远离故土而得的安全感,比重逢更重要。

一个时代的分崩离析,让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被迫改写。于凤至选择在美国度过后半生,未必荣耀,却足够清醒;张学良携在夏威夷安度晚年,也算得偿心愿。至于旁观者的评判,不过是后话。
驰盈策略-驰盈策略官网-专业配资公司-广东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